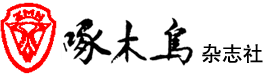在信息通畅、知识裂变的时代,任凭包括“妇孺”在内的人们“知道”什么都极为正常;倒是“不知道”什么会让人觉得奇怪。比如,你不知道那几位唱响歌坛、红遍荧屏之星的名字和隐私,不知道哪个地方爆出了个什么“门”,不知道今年流行何种饰品、何种吃物,不知道“欧巴”、“菜鸟”、“灌水”、“拍砖”所指为何……即或不被怀疑是否“地球人”,大体也会被视为闭目塞听、不通世故的“冬烘”。
按说,这也是一种求知欲的高扬,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如同培根所说,“求知可以作为消遣,可以作为装潢,也可以增长才干”。有些“知道”,确实与增长才干无甚干碍,不过是为消遣心理与自我装潢所需,但你还是以知道为好,非独百无聊赖中得有所填补,更有谈天说地间得有所应对。设若场面上失去介入的谈资,又不愿寒蝉似的噤声,就容易屡生“局外”的尴尬。
这样的事碰到不少,私下以为该“努力学习”之余,也会有些“捍卫”意识萌生出来,甚至参照“知情权”一说,认定我们也该有个“不知情权”,该有些“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的勇气。有些东东我一定要知道吗?我可以不知道吗?一方面,不知道那些“星”们的名字,并不能跟“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同日而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门”,并不能与不知道二次大战等量齐观;不知道时兴时鲜,并不等于不知道时局时代;不知道新生的“第二汉语”,毕竟不是不通汉语。另一方面呢,知识如海洋,世情若转轮,连柏拉图都说“很可能我们谁都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知识……而我则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辈要说知道一切,其实大不实际而略无可能。
捣鼓出“不知情权”当然难免有点儿危言耸听,人们可以嘲笑“不知情”,却并不存在剥夺“不知情权”的事。问题在于这里的“嘲笑”本身其实包含了几许很为浅薄的自炫,包含了几多实属被支配的自得。据此觉得需要倡导一点“不知道”的勇气和自觉,盖因坚持自己的生活原则,本就需要一点儿“不通世故”。若言学有专攻、成就事业,爱因斯坦所言就忽略不得:“一个人只有以他全部的力量和精力致力于某一事业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为大学问者每每为世人看出几分“傻气”,大概正从一个方面注疏了个中原委。我们缺少的不是顺势应变的“事事通”,缺少的恰恰是那种不惮以许多“不知道”来求得或一“大知道”的智者的定力。
通常的情况是,我们过于介意一些“知道”。曾经看过几篇文字,字里行间分明带上一种讥诮,为了吃西餐不知哪个手拿刀哪个手拿叉,喝咖啡用了搅拌用的调羹进饮,学到了那点儿未见得没有必要的规矩时,联想到那一次陪几位意大利作家吃中餐,几位怎么也摆弄不了那双筷子,结果还是丢了筷子动手抓,抓得坦然。当下便义生题外地感慨,刀叉的拿法,跟从西人那里拿来一些好东西其实无大干涉,且西人不以用不了筷子自惭,我们却以用不对刀叉为羞,比较之下,可见为文者在讥诮国人“不知道”的时候,谆谆教诲中实在也透露出了一点儿他的“自卑心理”。
通常的情况还是,我们过于多了一点儿“知道”的自信。曾经见识过某些“访谈”,节目的主持人面对各行业的著名专家,按说是“访”者、“谈”者各就其位各尽其职,可主持人却每每越其位而去充当一位足以跟各路专家旗鼓相当的学术“研讨”者。不当插话时横插过来,没有疑问处平生枝节,凑趣打诨而喧宾夺主,专家们说些什么被弄得七零八落不得要领,能够凸显的则是主持者于党政财文、农工商学行行皆通、样样能说的假象。这不免让人疑惑,拥有话语权的时人“知道”得已然过剩而自认“不知”的勇气太过匮乏,这在鼓励了“全知全能”的自我表现欲、造就了“大胆”的同时也常常会造成“妄说”。我无意否定人可以“浅尝”、“粗知”更多的知识,只是想强调一个人更需自知、自制、自明,以利为“深入钻研”、“仔细揣摩”一己的“专门”提供必要的时空。
在深层的意义上,缺少“不知道”的勇气 ,不只是自我纹饰的肤浅表现,也是自我失落的内在因由。在“舍”与“得”的辩证题义中,“不知道”很可以看做是对“知道”的一种让渡。在“知无涯”面前,“生有涯”的人们,事实上如同罗素所陈:“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那伟大的放弃。”要求得某个方面的真知、深知,很该强化一点儿自己的“位置意识”和“范围意识”,守牢自己而摈弃诸多在与世揠仰、自我扩张中不必要的生命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