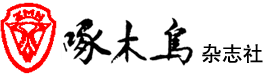到江西鄱阳采风,才知道历史上这里曾出过两个赫赫有名的文化人,一个是《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另一个是大词人、音乐家姜夔。
单说洪迈。当地人一提起他,立刻告诉你毛泽东主席几近弥留之际——临终前的十三天,还在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要看这部著作。这部书确实了得,它是作者集四十年之功,撰述的一部上自朝廷典章制度、治乱得失、经史诸子百家之言,下至山水风物、诗词文翰、文人逸事,内容广泛、考据精审的读书笔记,共五集,七十四卷,一千二百一十五条。第一集出版后,即得到当朝天子宋孝宗的充分肯定,认为该书“有议论”。到了后代,它的名气越来越大。明代河南巡抚、监察御史李瀚评论:“此书可以劝人为善,可以戒人为恶;可使人欣喜,可使人惊愕;可以增广见闻,可以澄清谬误;可以消除怀疑,明确事理;对于世俗教化颇有裨益!”它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首。
如此说来,称洪迈的学问独步当时是并不为过的,他确有些自负的资本。明人姜南在《风月堂杂识》一书中,就记录了有关洪迈自负的一则故事。说的是洪迈晚年做翰林学士,有一天在翰苑值班,为皇帝草拟诏书,从早晨到下午竟然写了二十多篇,非常忙碌。完事后他在庭院里散步,看见一位老人坐在树下晒太阳,就跟他聊了起来。原来老人家几代人都在翰苑当差,年轻的时候还伺候过元时期的前辈。老爷子首先奉承洪迈说:“今天文书这么多,学士一定辛苦。”洪迈很得意地说:“今天写了二十多道文件,都交差了。”老爷子忙恭维说:“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呢。”洪迈不由自负地问道:“当年苏东坡苏学士,都说他笔头快,也就这么快吧?”老爷子点点头,说:“苏学士敏捷,也就这么快了,”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不过,他草制诏书的时候是不用翻书的,都在脑子里装着呢,不至于像您这样费劲噢。”闻听此言,“洪为赧然,自恨失言。尝对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你看,洪迈的学问够大的了吧,可是与苏东坡一比,他羞得都要钻地缝。他确有自负的一面,但当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却翻然醒悟,“人不可自矜”,这一点清醒的自我认知,对他日后的笔记撰写能没有帮助吗?
说到苏东坡,就更有趣了。不知是吃东坡肘子太多还是喝酒太多的缘故,东坡居士的肚子里是颇有些油水的。在他还没有彻底倒运、被发配到海南之前,有一天他跟家中的歌妓们饮酒,拍着自己的大肚皮,问歌妓们:你们猜猜看,我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有的猜是学问,有的猜是经纶,有的猜是智慧,独有苏东坡最喜欢的小妾朝云说:相公肚皮里没有别的,只有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东坡听了,哈哈大笑,称赞朝云确是红颜知己。何谓“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你想,王安石提倡变法的时候,苏东坡认为某些改革措施没有便民而是扰民,受到改革派的排挤;朝廷要求完全废止新法的时候,苏东坡却站出来称颂改革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利益,使老百姓得到了某些实惠,这无疑又让保守派心中不快。到头来,苏学士两面不讨好,岂不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吗?我想当苏东坡拍着肚皮询问下人的时候,他的心中一定是颇自负的——为自己的道德学问,也为自己的官场政绩,可是朝云的话触动了他心底最真实的那根弦,唤醒了他的自知,这才有对红颜知己的大加赞赏。
当代的例子不妨举钱钟书。钱先生的《管锥编》据说征引了中外四千余位作家的上万种作品,涉及七种外语,有关他的自负有很多传闻,比如他说过陈寅恪做学问太琐碎,说过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自己也懒得去拜访。其实,不是他看不起司马迁、韩愈,而是为了节省时间,好一本本地读自己想看的书。他当然有资格自负,可是另一方面,他与不少素不相识的后生晚辈进行着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比如,年轻学子刘永翔为钱先生提供了一条支遁好马、养鹰的资料,钱先生立刻在《谈艺录》增订本补正中标出刘君大名;安徽一青年告知钱先生可查到赵汝鐩的生卒年,钱先生立刻通知日译本《宋诗选注》标出是该君告知;傅璇琮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对钱先生帮助甚大,钱先生在《谈艺录》修订本中提到的现代人只有两处,一处是吕思勉,另一处就是傅璇琮。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大凡有才的人,总是有一些自负的,所谓恃才傲物,说的就是这类人。但如果一味自负,像尼采那样,以为高出世人四千英尺,那结局并不美妙——只有发疯;更多的天才是像爱因斯坦那样,发现自己对宇宙认知的越多,不懂的也就越多。世人常见只有半吊子人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真正的大学者只有谦恭、平和,这不是作秀,而是他们的精神到达了这样的化境。